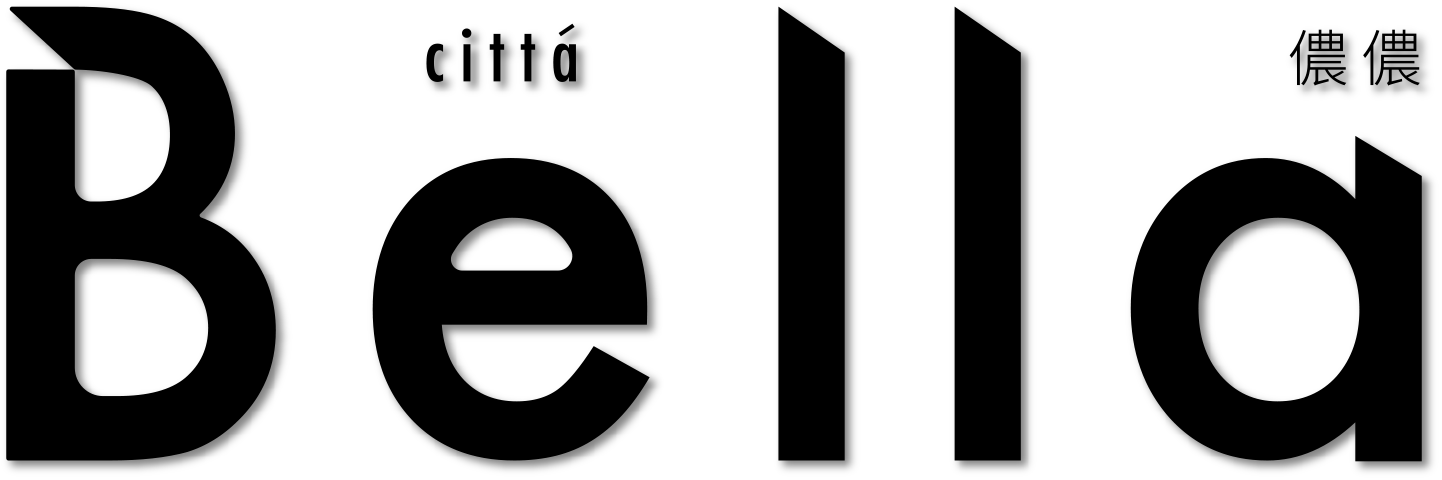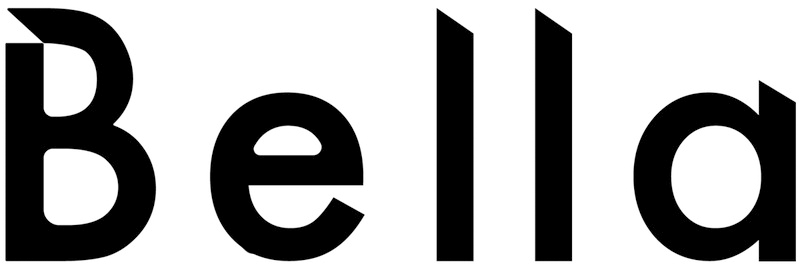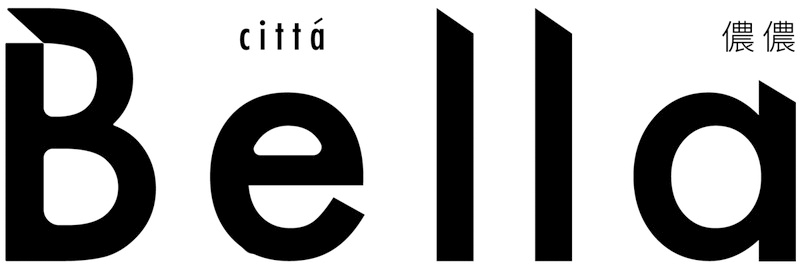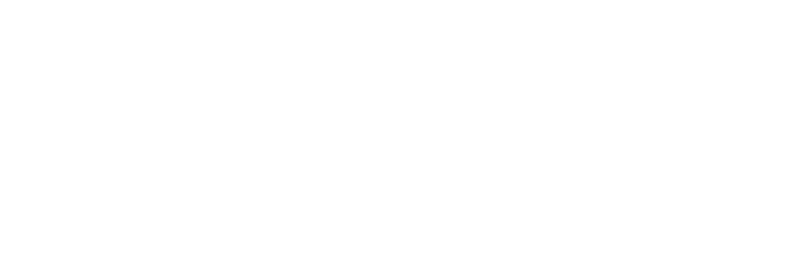鈴鈴──超市歡迎客人的廣播聲響起,傍晚時刻人潮眾多,一對看似父子的搭檔正著手某項計畫,趁著店員忙碌之際,小男孩打開空背包,熟練地進行「填充」任務,順利結束後,他們宛如普通人一般地走出超市。
冷颼颼的傍晚,回家路上兩人又聽見往常的聲音,那名小女生獨自在家玩耍,看似好幾天沒吃東西,於心不忍的男人帶著她回到家中,與家人一起吃晚餐。
.jpg)
家族成員有奶奶、一對伴侶、少女和小男孩,這些人沒有血緣關係,卻住在一起如家人般地互動,長久下來,小女孩身上被家暴的傷痕,也逐漸因這家庭的溫暖而復原;然而,卻在一場偷竊意外導致這層關係的破滅,警方介入調查之際,觀眾才逐漸明白這些人的背景,不堪回首的過去,如何造就了他們的人生走向,絲絲入扣著心弦,片尾結束,不禁仍會想著──如果我是他們,會是什麼樣的人生?
本部片名預告了「偷竊」與「家人」的意涵,根據導演是枝裕和先前「家人主題」的作品,皆有一個共通點,那就是「境遇」。
.jpg)
若要說明得更詳細,可以參考許多台灣社會新聞的面貌,例如:拋下二子而自殺的父母、家人疏於照顧嬰兒導致死亡、慣竊父母帶著孩子一同行竊等等,而導演精準地剖析個案中的家庭問題、社會問題,以溫柔的影像故事包裝而成,帶領觀眾體會箇中意義,大概是本片成為坎城影展金棕櫚獎項的最佳原因。
以下為(不劇透但沾邊的)私人推薦的理由。
身分:何以稱為「家人」?
目前我們所處的台灣社會,絕對認同、大多認同與少數認同的「家人」身分,如下:血緣>領養>同居 (不限於伴侶關係)。
以上用詞可能不精確,但仍能想像得出來,首要是血緣關係的家人,由於父母是生下孩子的人,因此絕對認同「家人」的關係。
.jpg)
其次,領養雖無血緣關係,但於法律上正式成為「家人」,因此也被社會大多數人所認同,此指的是大多數人於社會、心理層面皆認同的意思,「家人」關係也是「正常」的。
再來是同居,伴侶、非伴侶者,長期同居於一屋簷下,並照顧彼此生活起居,長久下來,伴侶即便沒有正式登記結婚,或非伴侶者也有另一半,但彼此不長住在一塊,而同一「住處」的人們,產生「家人意識感」,也少數被社會認同為「家人」,但這樣的情況會有許多組合,便不贅述。
.jpg)
看完整部片子,很難不去捫心自問:究竟什麼樣的關係才能稱得上「家人」?
擁有血緣關係但時常受到家暴的孩子,能稱家暴者不是「家人」嗎?
沒有血緣關係,可總是受到他人照顧的孩子,能稱照顧者為「家人」嗎?
片中堆疊的情感成為複雜的原因,倫理道德、身分定義以外,最難釐清的或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,有太多情況無法被歸類於「某一種」,也因此形塑了《小偷家族》無法抗拒的魅力,一切的奠基皆在於「人」。
.jpg)
故事描述「境遇」的細節,哪些人一路被社會無視,因此人生下墜不起,哪些人嘗試重新回到社會,但卻數度遇到困難,眾多被「境遇」掃到社會邊緣的人們,努力地抓著邊緣,祈禱自己不被完全拋棄,卻又不斷萌生墮落的想法──有的人撐得過去,卻有太多人活不到撐過去,始終掙扎。
《小偷家族》最終仍有一束光線,即便被塑造的「家人」關係已破裂,也看似分道揚鑣,但那段時光仍在屋子裡流轉,難以忘懷也無法忘卻的情感,已不是「家人」的味道,而是超乎「家人」的存在了啊。